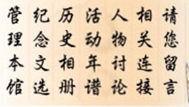我的父親名士松,字鑑,號鏡之,1909年6月15日生於上海殷行。我的先祖是明朝的御醫,獲明朝皇帝賜封於此,所以家中有不少醫書和招牌,後來被我的祖父當柴薪燒掉。日本侵華期間,把我家的墳山闢作軍用機場,也就是現在的江灣飛機楊,掘出之石棺,明代先人之遺體,身穿朝服,仍栩栩如生者。解放後,我家的袓屋也被拆建成水電廠工人宿舍。祖父原姓陳,名嘉言,是一名裁縫,由於殷家長房沒有男丁承祚,於是由族中長輩決定從遠房親戚陳姓族人中選一男丁入贅。辛亥革命軍興,祖父嘉言公是黃興部下的一名軍官,因為作戰有功,曾經獲得黃興親頒勳章與指揮刀,在抗日逃難時棄於黃埔江。
祖父生有二男二女,辛亥革命成功後,在家中開了一間輾米廠。父親是長男,中學時在師範中學讀書,於1927年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並於復旦大學任地下刊物“飛石”的主編,有一次,父親在復旦的飯堂用膳,國民黨特務進入飯堂大喊父親的名字,父親於是從飯堂的後門逃走,父親在復旦大學只讀了一個學期,後來進入大夏大學又讀了一個學期後,又因國民黨的緝捕而停學。
父親作為文藝青年常於內山書店與左翼文人交往,並被周楊評其詩作形似口號,嘗參與組織多次街頭暴動:先在街頭放下手絹,然後演講,待籌得一定款項後將硬幣用手絹包好,用作敲破汽車玻璃之用。
有一次國民黨特務來到家中捕獲父親,時值冬天,袓父要求特務讓父親到樓上更衣獲准,於是父親在姑母的協助下拆掉與隔壁相間的木板(隔壁住的也是親戚,論輩份可算是我的太姑婆)從隔壁逃走,於是特務把我的袓父捉走並刑求,想調查父親藏匿的地方,當我那個在國民黨上海黨部任職的叔父保我袓父回來時,袓父已經是奄奄一息,沒有多久也就離開人世。
抗戰期間,國共合作抗日,父親任上海郊區十多個縣的負責人及游擊武裝的參謀長。有一次父親在船上因膚色黝黑形似軍人而被日軍捕獲,後查出父親的身份,誘降不果,準備擇日槍決。父親被日軍單獨囚禁於一間民房,四周有日軍看守,父親於是數自己的脈搏來計算日軍的巡邏時間,並用自己的小便澆濕牆角挖洞,於一個風雨之夜脫光衣服逃走。
逃走時,父親需要跳下城牆(兒時,父親就要我練習從高牆上跳下,說是急時有用),因日軍出動軍犬追捕父親,父親不懂游泳,於是口啣麥管藏在護城河中,當父親回到家中,家人正為父親準備後事。
解放前,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徐晚楓(原為中共黨員,被捕後叛變)找到父親,說全國通緝令已下,正扣在他手中,要父親立即隨他到機場,否則三日後即予拘捕,父親遂由滬抵港,未幾閱報,果見刊有通緝段士林的通告。解放後,有關方面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監獄中發現其上司陳沬(亦原為中共黨員,被捕後叛變)已發漲的屍體。
解放後,父親送大哥回上海讀書,組織力勸父親留滬工作,遭父親拒絕,父親其後在澳門定居。
父親在上海時,因工作需要,曾獲組織授以白朗寧手鎗二支,已於離滬前交回組織,因此事,害得大哥在文革時幾乎跳黃浦江,因為紅衛兵要大哥交出這兩支手槍。
父親在1970 年7月10日因胆汁倒流,失醫而死,當時正被澳葡當局以莫須有罪名,未經審訊,被長期非法拘禁於氹仔社會復原所(此地原為一戒毒或精神病治療之地,而先嚴既非癮君子亦非精神病患者)。
父親曾被國民黨反動派拘捕而沒有死,曾經被日寇拘捕而沒有死,曾經被汪偽政權拘捕而沒有死,而死在澳門的”愛國同胞”串通澳葡當局的非法拘留中,而父親窮數十年精力的有關哲學及博奕學的研究成果,澳葡"治安警察"答應看管的父親所遺下的數十箱書稿亦不知下落。
在澳門回歸前,我曾向澳萄“申訴專員公署”提出申訴,被當時的有關當局以案件超過刑事追溯期為由拒絕聲請,而無視我一直為此事向澳葡有關當局提出申訴的事實,其後曾向澳葡的“法院”提出民事申訴,至今未見其回覆,這是一件有關人命的案件,這筆帳我是一定要算的。
祖父生有二男二女,辛亥革命成功後,在家中開了一間輾米廠。父親是長男,中學時在師範中學讀書,於1927年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並於復旦大學任地下刊物“飛石”的主編,有一次,父親在復旦的飯堂用膳,國民黨特務進入飯堂大喊父親的名字,父親於是從飯堂的後門逃走,父親在復旦大學只讀了一個學期,後來進入大夏大學又讀了一個學期後,又因國民黨的緝捕而停學。
父親作為文藝青年常於內山書店與左翼文人交往,並被周楊評其詩作形似口號,嘗參與組織多次街頭暴動:先在街頭放下手絹,然後演講,待籌得一定款項後將硬幣用手絹包好,用作敲破汽車玻璃之用。
有一次國民黨特務來到家中捕獲父親,時值冬天,袓父要求特務讓父親到樓上更衣獲准,於是父親在姑母的協助下拆掉與隔壁相間的木板(隔壁住的也是親戚,論輩份可算是我的太姑婆)從隔壁逃走,於是特務把我的袓父捉走並刑求,想調查父親藏匿的地方,當我那個在國民黨上海黨部任職的叔父保我袓父回來時,袓父已經是奄奄一息,沒有多久也就離開人世。
抗戰期間,國共合作抗日,父親任上海郊區十多個縣的負責人及游擊武裝的參謀長。有一次父親在船上因膚色黝黑形似軍人而被日軍捕獲,後查出父親的身份,誘降不果,準備擇日槍決。父親被日軍單獨囚禁於一間民房,四周有日軍看守,父親於是數自己的脈搏來計算日軍的巡邏時間,並用自己的小便澆濕牆角挖洞,於一個風雨之夜脫光衣服逃走。
逃走時,父親需要跳下城牆(兒時,父親就要我練習從高牆上跳下,說是急時有用),因日軍出動軍犬追捕父親,父親不懂游泳,於是口啣麥管藏在護城河中,當父親回到家中,家人正為父親準備後事。
解放前,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徐晚楓(原為中共黨員,被捕後叛變)找到父親,說全國通緝令已下,正扣在他手中,要父親立即隨他到機場,否則三日後即予拘捕,父親遂由滬抵港,未幾閱報,果見刊有通緝段士林的通告。解放後,有關方面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監獄中發現其上司陳沬(亦原為中共黨員,被捕後叛變)已發漲的屍體。
解放後,父親送大哥回上海讀書,組織力勸父親留滬工作,遭父親拒絕,父親其後在澳門定居。
父親在上海時,因工作需要,曾獲組織授以白朗寧手鎗二支,已於離滬前交回組織,因此事,害得大哥在文革時幾乎跳黃浦江,因為紅衛兵要大哥交出這兩支手槍。
父親在1970 年7月10日因胆汁倒流,失醫而死,當時正被澳葡當局以莫須有罪名,未經審訊,被長期非法拘禁於氹仔社會復原所(此地原為一戒毒或精神病治療之地,而先嚴既非癮君子亦非精神病患者)。
父親曾被國民黨反動派拘捕而沒有死,曾經被日寇拘捕而沒有死,曾經被汪偽政權拘捕而沒有死,而死在澳門的”愛國同胞”串通澳葡當局的非法拘留中,而父親窮數十年精力的有關哲學及博奕學的研究成果,澳葡"治安警察"答應看管的父親所遺下的數十箱書稿亦不知下落。
在澳門回歸前,我曾向澳萄“申訴專員公署”提出申訴,被當時的有關當局以案件超過刑事追溯期為由拒絕聲請,而無視我一直為此事向澳葡有關當局提出申訴的事實,其後曾向澳葡的“法院”提出民事申訴,至今未見其回覆,這是一件有關人命的案件,這筆帳我是一定要算的。